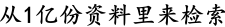- 韩非子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阅读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曾子杀彘》的内容令我印象最深。 《曾子杀彘》讲述的是曾子的妻子出门买东西,儿子缠着也要去,于是妻子骗他说,他不跟着去,回来就给杀猪给他吃。儿子就留在家里。曾子回来听说了此事,就
韩非子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阅读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曾子杀彘》的内容令我印象最深。
《曾子杀彘》讲述的是曾子的妻子出门买东西,儿子缠着也要去,于是妻子骗他说,他不跟着去,回来就给杀猪给他吃。儿子就留在家里。曾子回来听说了此事,就要去杀猪,妻子拦住了他说只是骗儿子的。但曾子还是把猪给杀了。
曾子做到了讲诚信。
记得有一次,妈妈让我去买豆腐。我来到卖豆腐的阿姨摊前,说:“要两块豆腐!”阿姨一听,顿时就来了精神,装了两块豆腐给我,还找了我一元一角。我看到那一角钱,心想一角钱算什么?能买到什么?于是就不屑地说:“阿姨,这一角钱就给你了吧,我不要了!”阿姨听了,对我说:“干我们这行的,哪能多贪图你的钱呢?做人要讲诚信。”我听了,红着脸低下了头,拿了钱,脚踩西瓜皮似的溜走了。
这时,门口传来了几声敲门声,我走过去打开门。一看是阿姨,正愁一肚子气没处撒,刚想破口大骂,阿姨气喘吁吁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让你拿一角钱你就不拿一块钱呢。”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说不出话来。阿姨把一块钱塞在我手里,转身就走了。等到阿姨的身影消失在转角的地方,我才回过神来,有些结巴得说了句:“谢……谢谢阿姨。”
原来是我错怪阿姨了。
我想:阿姨不就是“曾子”吗?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们带着诚信,与诚信同行。
韩非子读后感篇二
《韩非子》里有个“智子疑邻”的典故,现在常被用来讨论感情亲疏对认识事物准确性的影响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挺浅薄,也不那么让人信服。
就按照那故事本身来说,事情发展的结果根本不用说,这还用想吗,就想电视剧的剧情一样,当然是打110报警直接把邻居当嫌疑犯啦,难道还能怀疑自己儿子不成?把自己的儿子当贼看,落下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的骂名吗?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们假设,事情的真相就是是儿子监守自盗。那么,我的意思也仍然是,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个结果,宁愿永远停留在对邻居错误的怀疑中。
对所谓真相的探究,真的就比情感的平衡来得重要?我想那个父亲也和我想法一样,可能韩非子的故事里面就真是儿子偷的,父亲早就知道了,可是,不是邻居,就是儿子,换了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断定邻居就是小偷。什么六亲不认,法理难容,别再说这一套了,都是口头话,到时还不是侧着脸,一面不忍地举报邻居。这是情感作的怪,那血融于水的'感情啊,每个人都宁愿内心愧疚一辈子,也不想看着亲人的落魄痛心揪肺。
深奥的我不会,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篮球。现在假设中国队要再跟美国队打一场球,你让我下注,押哪个队?你尽可以告诉我中国队一直没赢过美国一场球,你尽可以告诉我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你甚至可以告诉我半场人家已经大比数抛离了,可我跟你说,我死活就是要押中国队!尽管姚明打不进篮下,尽管大郅被人压着来欺负,尽管全队完全没有了脾气,可是,我依然会支持他,也会千辛万苦地挑出他的好,姚明盖了美国人的球,大巴把对手撞得满地找牙……我喜欢nba,喜欢看美国球星打球的激情,但这都不影响我对中国队的支持,这就是情感作的怪。
我时常怀疑,现代人是不是过于聪明了?亲兄弟算账,有纠纷也不找老长辈调解,却喜欢直接奔法院了;夫妻间要自由,出现问题也不再宽容忍耐了,干脆搞离婚二次选择;在网上看到甚至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号召学习西方家庭,孩子长到18岁再要钱就给爹妈写借条了!你看,我的天啊,多少愚昧的行为,打着理性的旗帜,冲破情感的脆弱防线。难道那一切无谓的东西,竟比感情更重要,比能相聚在一起的缘分更矜贵吗。
我是个愚人。我自以为所谓理性或真相,永远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因为人间有情。时常听到一句话叫“情有可原”,就算是最严明公正的法院审判官,也都一样受到情感的左右。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父母,相信我的姊妹和朋友,相信尽管我错了,他们一样会在背后支持我;我相信善良,相信真诚,相信这些信仰本身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
韩非子老人家留下这个典故,所要告诉后人的真正意思,就真是要见仁见智了。我宁愿相信俄罗斯一位智者所说:理性是苍白的,而情感之树常青。
韩非子读后感篇三
所谓“利民萌便众庶之道”,就是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现代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法治。《韩非子》一书,就像是韩非在封建社会的大框架下,以“法、术、势”为核心的一本“政法大纲”。
以我,一个初中生的思想来看,韩非的政治主张与其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最大差异在于“法治”和“礼治”两个概念。
韩非本人从他选取的故事来看,是想要证伪儒家在《论语》中记载的关于仁义治国的观点。比如《难一》里讲到的历山的农民与舜,韩非通过一系列关于尧,舜两个圣人的辩证,揭示了他们两人都被儒家称为圣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引申到一个治理天下的人“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像中山国国君那样(也像儒家提倡的那样)“好岩穴之士”的话,那么《经四》里说的“中牟之异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的事就一定不可能避免。而这个观点在书中被反复提到过,像“齐王好衣紫”和“邹君服长缨”这些故事就让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显得黯淡无光,更加衬托出了韩非对于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中君主的定义:“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第三点,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部分:法、术、势和包括《定法》,《有度》,《八经》,《用人》等十四篇的建国纲要。法,在书中的意思就是法律。术,据书中观点是君王心中必须要掌握的用人知道。势,就是自己的权势。这三者在建国,强国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我把这些转换成通俗语言,就是依法治国,善用人才,群众路线。法,在本书中正好有一句概括性的介绍,就是:“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奖赏不用太丰厚,让人民有追随利益的感觉就行了,名誉不用太高上,让民众有荣誉就行了,声讨不用太激烈,让民众害怕就行了,处罚不用太恶劣,让民众有耻辱就行了。这是韩非运用人们的心理习惯总结出的立法原则。而法在文中的解释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君主给臣民们的规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术就是现代的用人法则一样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发现好的人才后,要先让他在基层锻炼,并考核他的能力。这一点,韩非能这么早想到,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儒家学说提倡的“直接任用贤人”的错误理念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而势的定义,给大家举个书中的简单例子:如果桀纣生来就在君位上,而尧舜则生来是贱民,那么桀纣在统治时,天下有十个尧舜也不能安定国家;而如果反之,尧舜生来在君位上,而桀纣生来是贱民,那么有是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国家的秩序。
《韩非子》在文学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内、外储说》的寓言故事。在法律界的件数则是真正法治意义的提出者。韩非本人也是一个敢于实践的人。新世纪,许多古代的学说,例如儒家和道家,都已被重新发扬,我们希望对于同样在诸子百家里有重要地位的法家,也有这样经过去其糟粕,取之精华之后的重新复生,“古今异俗,新旧具备”!
韩非子读后感篇四
《韩非子》是一部传递法家思想的历史名著。现在我用最淳朴的语言来向你介绍《韩非子》中的四则寓言故事。
一: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
这篇短小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经韩非子所说,又经历考证,韩非子是为了告诫君主:“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说一些漂亮动听的言语,君主往往只看到了它们表面的文采而忘记了它们是否有用”
二: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其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这篇幽默的小短文,在我看来,这是韩非子要告诫人们若要灵活干事,不能像郑人一样固执,在生活里,不能受某样东西约束自己,那么你最后必定会闹出一个像郑人一样的大笑话,更深层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注重尺码这样物体的表面。
三: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此故事短小精悍,一语道破,告诉了人们要做一块真材实料,不可以像南郭处士一样,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另外,此文章还从侧面批评了当时君王的昏庸无能,为了一个处士,在民间搜刮几百人的粮食供处士享用。
四: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
《韩非子》虽然非儒家文化,但其反应的道理本质未改,对做人很有帮助,希望更多的人去体验一把法家文化。
韩非子读后感篇五
七种安术,前三种讲赏罚、祸福、死生各自依据的标准,第四和第五种讲贤不肖和愚智在君主择臣时的重要性,第六种说明君主一切行事都须遵从规矩,第七种说明君主施政要注重诚信。六种危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必须依法行事,不可破坏法制;第二、行政应顺应人情的自然,不可肆意妄为。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法治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因素,首先在于统治者破坏法制。一个社会的法制被破坏了,为政者随意妄为,必然使整个国家走向危亡。所以,七种安术,前三种和第六种主要强调治国行政应当有法度规矩,任何情况下不能凭借一己的主观情感和臆断。
用人方面,韩非所强调的同样是“有尺寸而无意度”。韩非认为,贤能和不贤能是需要通过办理具体事务的检验加以判定的,绝不可以凭借君主喜爱还是厌恶。
第七种安术讲诚信,这也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因为法无信不立,君主言出必行,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信赏必罚的牢固信念,而赏罚是法令的核心内容。诚信和法令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君主倘若靠欺骗愚弄百姓来行政,也就意味着摧毁了君主和法令的权威,可以得逞于一时,但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而且一定不可能长久。
韩非讨论安危之道时,着重分析了法治与人心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这符合人情人心,因为人们更喜欢在安定有序的社会中生活。法律是达到安定有序的有效手段。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忠于法律,他制订的法律忠于民众的心愿,所以用它来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去掉了它,民众就会思念。)。
如此说来,“利人之所害”云云,其实都是指君主做事颠倒是非,无法无天。人们朝不保夕,自然“不乐生”“不重死”。一个民不乐生、民不重死的国家,其安危也就不言而喻了。
韩非子读后感篇六
《韩非子》就是一种悲观哲学。
任何一种思想,都能解释身边的世界。
《韩非子》就是一种悲观哲学。
单纯的人看这本书,自然大摇其头,骂道这真是畜生写的书。
可是,单纯是一种恶,是比邪恶还要严重的恶。
自己选择邪恶,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能解释的通;而单纯人做下了事情,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比如十字军里面单纯的骑士们。
人性本恶。
所以要提放身边的大臣、妻妾、儿女。
“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我不是相信你的忠心,而是相信你不敢背叛我。
孤独的王,冷酷的王,忧伤的王,强大的王。
这就是韩非子所假想的王。
韩非不相信人。
不相信有幸福存在。
韩非只相信人是弱肉强食。
韩非对人的认识是,人是一种趋炎附势的动物,人为了自己什么都可以出卖。
人是什么,《商君书》中有言,“民固服于势,寡怀于义。”老百姓只是服从权势,而不感恩仁义。
《韩非子》中举了很多例子,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鲁国国君的园林失火,士兵都去抢财物。
国君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谁救火我就赏谁?旁边的人说,不能赏赐他们,要下命令说,谁不救火我杀谁。
命令下达,果然火被救了下来。
考虑到现实,我不得不说,韩非子说的对。
人就是这样的吧。
只会考虑为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不会想到报恩。
韩非子想,既然如此,请允许我以天下人为刍狗。
信任在韩非子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孔子讲“忠恕”,而在韩非子看来,全是不干正事的吃闲饭的人。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人与人之间,就是血淋淋的利益。
我有难,你只会趁火打劫。
读完《韩非子》,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我还准备找《商君书》、《战国策》、《左传》、《资治通鉴》等书来看一遍。
可是我和朋友聊了一次天,我动摇了。
我很崇拜武则天,我就说,现在穷人家的女孩子,尤其这些女大学生,我的女同学们,不要再和穷小子花前月下了,赶紧嫁入豪门才是正事,嫁入豪门就要开始积蓄力量,准备夺权。
就像武则天一样。
可是朋友说,人生应该是和妻子感情深厚,朋友你来我往,孩子健康成长,武则天是很可怜的人。
朋友认为这才是正常的人生。
他认为我想的东西太偏离“现实”了。
而我认为他想的东西太理想化了。
我们都认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实,对方的是“幻觉”。
我疑惑了。
人生到底该怎样?幸福为何那么远?我也开始心慈手软了。
我不再那么冷酷不爱笑了。
我也开始不再一个人读《韩非子》了。
我的观点受到了朋友的影响。
我也开始想信任人了。
这样下去,我做不了事业。
记忆中,很久前的我,也是爱笑,爱交朋友,爱玩,爱睡觉,爱起哄的人。
我说不清是对是错。
我该相信什么?我该相信“真情”吗?我该怀疑吗?
我怀疑很多东西的存在。
道德,爱情,亲情,友情,事业,幸福。
我一一否定了这些。
我看到弱肉强食中强者就是道德,“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爱情,贪婪的父母和痛苦的子女构成了所谓的亲情,用过就扔的朋友,邪恶中诞生的事业,一只heroin就可以解决的幸福。
是我太单纯,还是什么原因?古人说,“明哲保身”,明白道理,是为了保全自己的。
自己最重要吧。
如果信仰受到他人的侮辱,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
如果信仰受到自己的怀疑,我真的坚持不下去。
我该相信什么呢?
世界中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杀戮,还是仁慈?
每一个通读过《韩非子》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所吸引。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浩瀚的思想史星空里,韩非子的思想始终耀眼,虽不如儒家思想那样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思想那样被文人志士推崇,但却真真正正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今日仍未磨灭。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思想,把商鞅的发“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结合在一起,明
本类下载排行
-
2023年对孩子的评语(通用13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对孩子的评语篇一 1.学习中你能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你永不落败的秘诀。老师希望你能借助良好的学习方法,抓紧一切时间,笑在最后的一定是你。 2.你是个聪明自信的 ...
-
最新设计课程心得体会 ci设计课程心得体会(实用13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 ...
-
2023年合同书样本完整版(实用16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合同书样本完整版篇一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经协商达成一致,签定本合同,由双方共同恪守履行协议条款。 ...
-
最新运动的心得体会 运动社心得体会(优质8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
-
运动的心得体会(优质20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运动的心得体会篇一 运动是一种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活动,而参加运动社团更是能使人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获得更多的收获。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运动社团 ...
-
2023年冀教版一年级数学教案以内数的认识 一年级数学人教版教案(大全8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 ...
-
2023年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优质12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主人公柴斯特和老鼠塔克,亨利猫还有柴斯特的主人玛利欧。书中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捡到了一只叫柴斯特的蟋蟀,小 ...
-
最新成绩的心得体会(优秀16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成绩的心得体会篇一 强化激励、发展功能,新课标指出:学生的学习评价应是对学习效果和过程的评价,主要包括体能与运动技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 ...
-
阳光教师心得体会(通用20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阳光教师心得体会篇一 一、引言(大约200字)。 教师,是承担教育重任的人,是从事教育事业的行业从业人员。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基本功,还要具 ...
-
最新银行活动心得体会 银行微课活动心得体会(精选17篇)
- 所属分类:范文资料
- 更新时间:2024-09-13
- 点击次数:10
- 银行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x月x日,我行在xxxxxxxx会堂召开了20xx年内控暨防案工作会议。xxx行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我入行x年来参加的规模最大,形式最 ...